本文于2021年1月4日发布于澎湃新闻,为澎湃商学院独家专栏“跨越不平等陷阱”系列之四。作者陈斌开,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高的不平等都不利于其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不平等程度整体都是攀升,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持续恶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程度也不断上升。那么,是否有可能逆转不平等上升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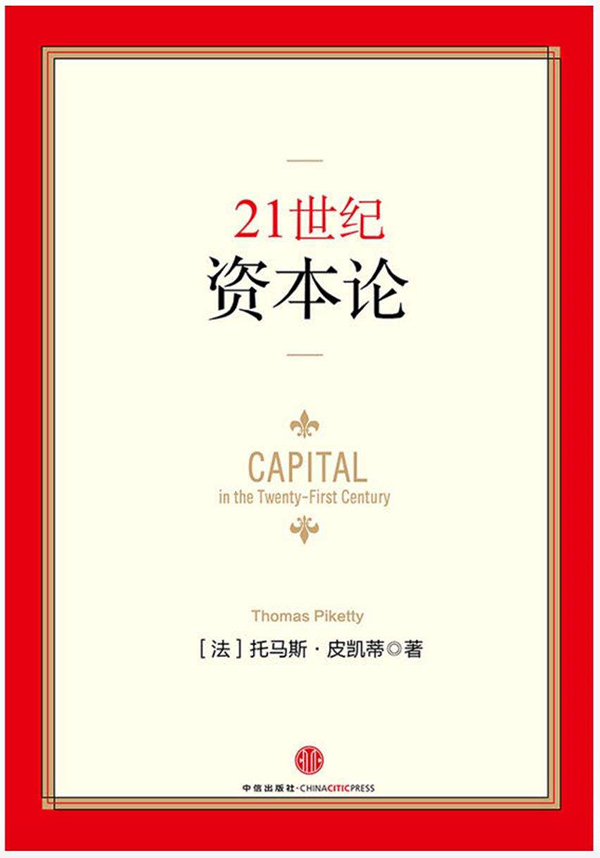
《21世纪资本论》,托马斯·皮凯蒂著,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版
近年来,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该书的主要观点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都有持续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很难逆转。仅有的逆转出现在1910-1950年间,其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极端破坏性的事件造成了不平等程度的下降,正常时代里,不平等程度都趋于上升。皮凯蒂进一步分析了不平等难以逆转的原因。他认为,导致不平等持续上升的力量是资本回报率r大于经济增长率g,所以资本的收入份额占比会不断上升,不平等会不断提高。
在全球不平等程度居高不下的今天,皮凯蒂的著作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全球的热议。这本书打破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即社会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发展先上升后下降)的乐观预测,认为不加干预的自由市场会造成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将这本书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或这个10年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但是,其发现和理论逻辑是真实正确的吗?
皮凯蒂对不平等现象的描述,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并没有持续上升,1950-1980年间,美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比较稳定,直到1980年以后才出现不平等程度持续上升趋势。
第二,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并非所有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出现上升,德国、法国、芬兰、瑞典、丹麦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并无明显上升,或者仅是温和上升。
第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四十多年里实行了“公平的增长”,即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不平等程度保持在低位,并没有出现不平等程度的持续上升。
第四,巴西、墨西哥等不平等程度偏高的拉丁美洲国家,在2000年以后不平等程度有了一定的下降。
同时,皮凯蒂对不平等上升原因的分析(r>g)理论基础不足,与经验事实也并不相符。从理论上讲,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会造成不平等上升。事实上,无论是在标准宏观模型中(假设每个人都是劳动拥有者,也是资本的拥有者),还是在资本-劳动的二元模型中(假设劳动者只拥有劳动,资本家只拥有资本),r>g都无法推导出不平等程度一定会持续上升。
为了让不熟悉宏观理论的读者能理解其中的逻辑,曼昆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Yes, r>g. So what?》)中,对皮凯蒂的逻辑进行了更加“形象”的质疑。假设一个富人生活在r>g的经济中,他能够将财产转移给他的后代,但是如果想要保证他的后代仍然很富有,他会面临三个问题。
第一,他的继承人会消耗他继承的一部分财富,除了食物、住所,还包括政治和慈善捐款,这对于富裕家庭来说是相当大的,对于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估计大约是3个百分点,那么财富的累积速度就是r-3。
第二,随着财富代代相传,它被划分给越来越多的后代,假设每一个后代都有两个孩子,那么每一代的数量就是上一代的两倍,由于世代之间相隔大约35年,后代的数量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因此,如果家庭财富的积累速度为r-3,那么每个后代的财富以r-5的速率增长。
第三,许多政府对遗产和资本收入都征税,假设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对遗产的总税收效应只有2%,考虑到税收效应,每个后代的财富增长速率就为r-7。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旦消费、生育和税收被考虑在内,如果想达到皮凯蒂资本不断累积而导致不平等无限增加的情况,只有r>g的条件是不够的,至少需要r-7>g。然而不管在过去还是未来,这种情况都是不可能出现的。
从经验事实上来看,r>g与不平等的关系也很微弱。Acemoglu基于Piketty的数据,对r-g与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之间不但没有正相关关系,在部分回归结果中还有微弱的负相关。由此可见,r>g也无法解释历史上不平等的变化。
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上,《21世纪资本论》似乎都存在很大缺陷,但为什么这本著作引起了如此大的关注?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上升的不平等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焦虑。皮凯蒂的分析尽管存在缺陷,但指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会造成不平等的持续上升,不平等一旦形成,要逆转就变得非常困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英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自由化改革以提高其经济效率。从经济发展绩效来看,自由化改革对维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却造成了不平等的持续上升。对于不平等的上升,早期很多社会科学学家抱有乐观的态度,认为经济效率的提升会导致带来更多就业,工资和收入水平上升,最终惠及低收入群体,即所谓“涓滴”(Trickle-Down)机制,不平等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涓滴”经济学曾盛行一时,包括皮凯蒂本人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对“涓滴”机制进行了诸多研究。然而,1980年之后的四十年里,美国最低收入50%的群体收入基本没有增长,经济增长的果实主要被高收入阶层占有,不平等持续上升,“涓滴”机制没有实现,《21世纪资本论》广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涓滴”经济学的破产。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要有效缓解不平等,实现公平的增长,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社会普遍认识到不平等对世界的危害,受凯恩斯等一大批思想家的影响,发达国家不断完善其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高收入群体税率大幅上升,政府福利性支出不断增加。
1950-1980年间,得益于其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制,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不平等程度比较稳定,实现了公平的增长。石油危机之后,由于经济效率下降,美国、英国实施了更为激进的自由化政策以提振经济,造成了不平等的持续上升。相比较而言,其它欧洲大陆国家自由化改革要温和的多,社会税收和福利体系得到了保留,德国、法国、芬兰、瑞典、丹麦等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在1980年之后也没有明显上升。
政府制度和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平等也同样重要。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增长,但政府对社会公平高度关注。日本政府大力投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建立了公平的教育、医疗体系,同时给予了农业部门大规模的扶持和补贴。韩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早期就实施大规模的“新村运动”,实现了城乡平衡发展。新加坡政府建立了覆盖全民的住房、医疗保障制度,确保了低收入阶层的机会均等。
相反,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实现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但其不平等程度也随之上升,之后很多国家陷入了长期停滞,“低增长、高不平等”成为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魔咒。进入新世纪以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试图通过激进的再分配政策改善其不平等程度,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其不平等依然处于高位,同时经济效率难以提升。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平等都非宿命,但是,要打破不平等的魔咒,政府的制度和政策至关重要。

 院长信箱
院长信箱
 书记信箱
书记信箱
 English
English